晨雾中的兴国站像一幅洇了水的水墨画。K743次列车缓缓停靠时,月台上"兴国"两个朱漆大字在氤氲水汽中若隐若现。我拖着拉杆箱下车,轮子碾过新铺的防滑地砖,忽然听见身后传来扁担"吱呀"的声响——回头望去,却只看见自己的影子,在晨光里与一个挑着竹筐的瘦削少年重叠。那是1982年的我,扁担两头挂着打了补丁的帆布包,竹筐里塞着母亲连夜烙的薯粉饼,油纸窸窣作响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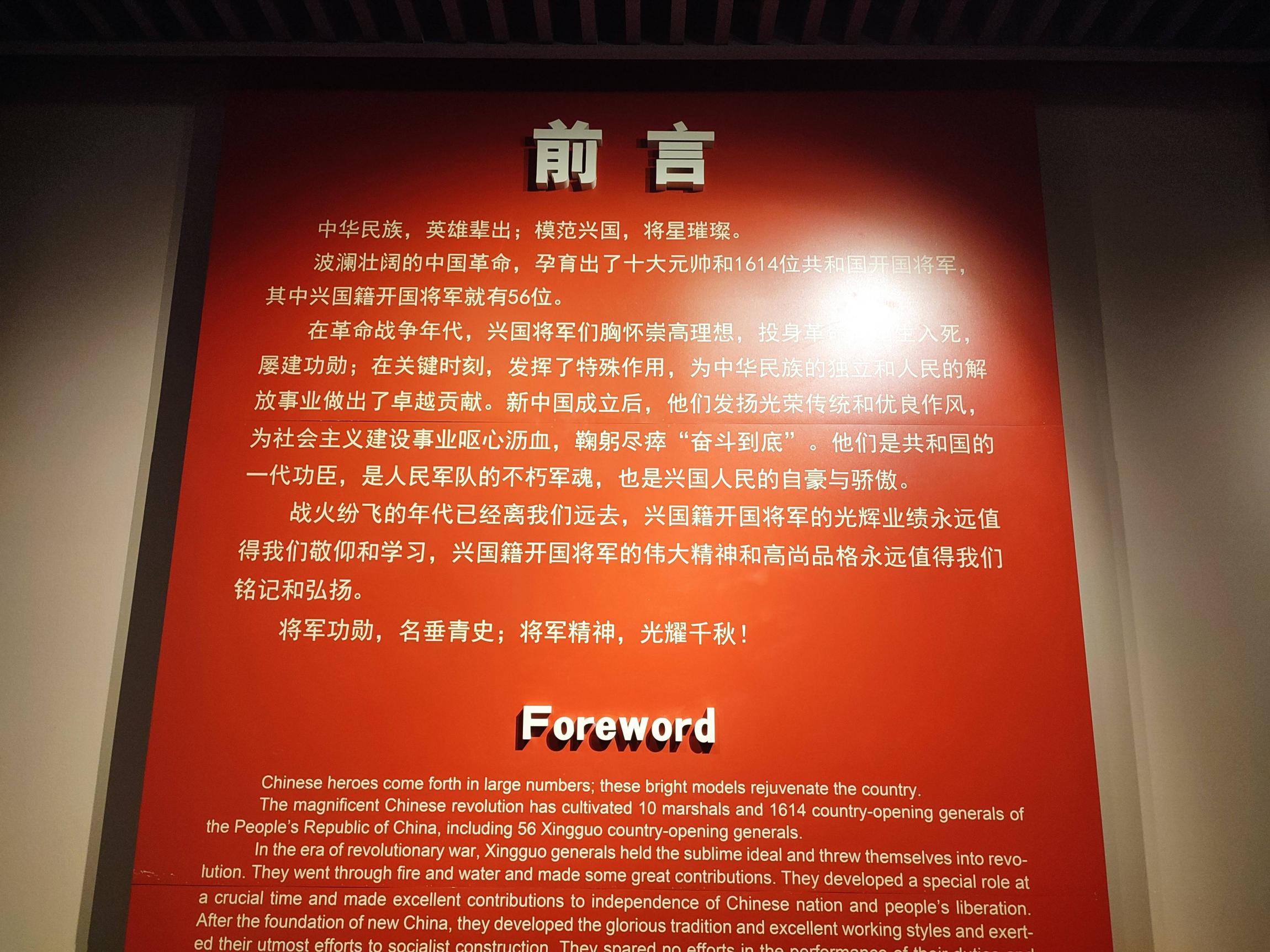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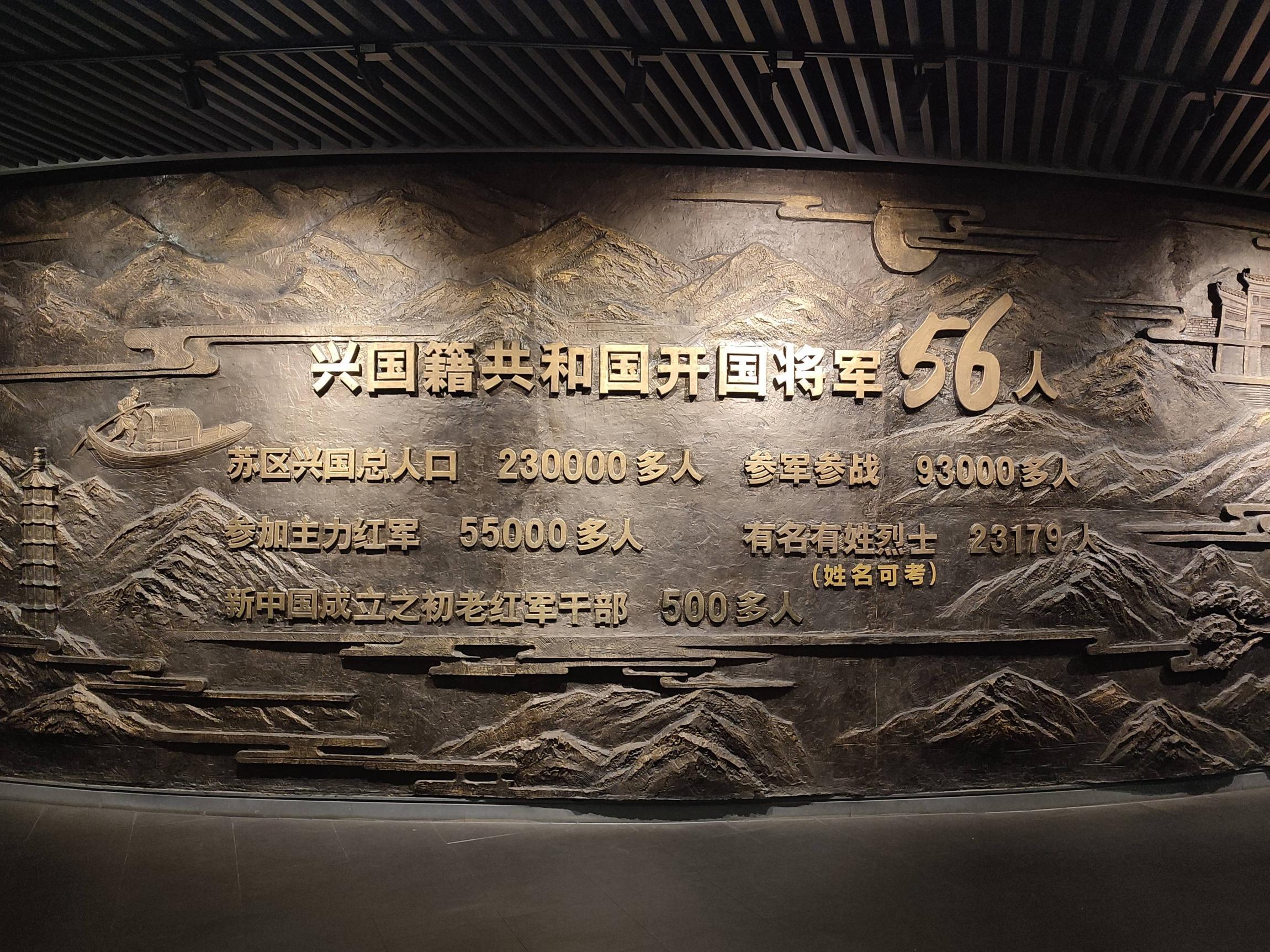
记得那年山道上的晨露总是特别重。十六岁的我踩着解放鞋,扁担在肩上烙下红痕,山风裹挟着钨矿特有的金属味钻进鼻腔。青苔在石阶上铺就柔软的地毯,每一步都惊起几只蓝翅蜻蜓。老营盘车站的条凳硌得人生疼,我蜷在墙角数着瓦缝里漏下的星光,听隔壁婴儿啼哭像把钝锯,生生锯断了夜的完整。
黎明时分,一辆墨绿色的老式客车喘着粗气进站。我把铁皮箱塞进货厢时,咸菜坛子碰出沉闷的回响,惊醒了货架上一窝麻雀,扑棱棱飞向泛着鱼肚白的天际。车厢里混合着旱烟、汗臭和晕车呕吐物的气味,却让我想起离家前夜,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衣裳时,针尖挑起的淡淡樟脑香。
兴国一中的老宿舍楼还在,米黄色涂料遮不住墙根蔓延的爬山虎。数到三楼第七扇窗——那年冬夜,我和陈志明就是从这里踩着冰棱溜下去,月光把水管照成一条银蛇。如今不锈钢防盗网割裂了天空,像给回忆钉上了牢笼。
教室里可升降的塑料桌椅泛着冷光。指尖抚过倒数第二排桌面,寻找那个被岁月磨平的"早"字。忽然记起某个霜晨,班主任的戒尺落下时,窗外油茶树上积雪簌簌,与我的抽泣同频共振。现在校史馆玻璃柜里的戒尺已成文物,旁边说明牌上"体罚工具"四个字,让当年的疼痛变成了展览品。
将军园所在的山坡,曾经是我们晨读的秘境。松针落进翻开的英语书,在"revolution"这个词上织出金色蛛网。如今那棵老松成了园区活化石,我们刻的"奋斗"二字被树皮包裹成凸起的疤痕。新栽的银杏还未长成,阳光穿过全息投影仪,在将军雕像群上投下流动的光斑,像给历史镀了层虚幻的金。
潋江书院的古柏依然苍翠,树皮皲裂如祖父的手背。记得老学究吟诵"先天下之忧而忧"时,总爱用戒尺敲打石桌,《阳关三叠》的节奏惊飞檐下筑巢的雨燕。如今石桌边立着的二维码标牌,扫出来的电子音冰冷标准,再没有当年戒尺敲出的错落韵味。
滨江大道的防洪墙白得刺眼。指尖摩挲着某块砖石上模糊的"6.13"——1983年洪水留下的印记,像首无题的诗。那年我们在淤泥里挖出的《代数习题集》,晒干后洇开的蓝墨水,如今化作纪念馆玻璃柜里泛黄的日记本上,一句"今日腰痛"的平淡记述。
红军大桥的落日依旧壮丽。江水把夕阳熔成滚烫的金汁,让我想起王建军跳水时,那片红色裤衩如何在江面绽放成木棉花。现在桥上的无人机嗡嗡作响,与当年我们惊起的白鹭,唱着不同的挽歌。
客家路骑楼下的老照相馆,如今飘着奶茶甜腻的香。我站在当年拍照的位置,背景布上的井冈山变成了电子屏里的元宇宙。穿汉服的少女们发间樱花摇曳,让我误以为是别在校徽上的玉兰,在1985年的春风里轻轻颤动。
平川中学档案室的花名册正在褪色。我的名字后面,"小龙钨矿"四个字淡得快要消失,像废弃矿洞里最后一点萤火。教导主任的红圈依然鲜艳,圈住那些飞出去的雏鸟,也圈住了某个挑着扁担翻山越岭的清晨。


暮色漫过兴国站时,霓虹给每个人的轮廓描上红边。K744次列车开始检票,电子屏的光映着旅客们的脸,像给旧照片手工上色的匠人,一笔一笔涂出失真的鲜艳。1988年离乡那晚,月台上煤油灯的光晕里,母亲塞来的冻米糖还带着灶台的余温。
列车启动的瞬间,窗外掠过挑扁担的幻影。玻璃窗倒映着我鬓角的白霜,与背包里油茶果的脆响应和,像那年雨季,教室漏雨的嘀嗒声。四十年的光阴在此刻对折,山还是那些山,只是风电机的叶片,正把我们的少年时光,一截一截锯成标准的千瓦时。








